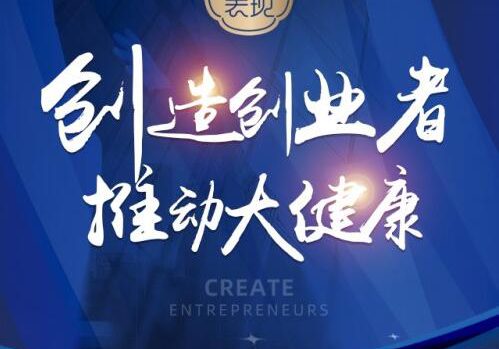头条
-
护航精彩全运,传递现金温度——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全...
随着第十五届全运会(以下简称“十五运”)在粤港澳大湾区火热进行,深圳作为核心举办城市,迎来各地运动员与游客。为保障赛会期间现金服务高效畅通,深化延续9月“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成效,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
城事
-
北京工业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未报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孔磊介绍,2月10日以来,本市工业企业逐步复工复产,截至目前,未报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13786
财经
-
北京将抽查核验核酸检测证明 如发现造假行为必查处...
进京人员入住酒店,应持有7日内经当地核酸检测呈阴性的健康证明。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本市将通过抽查、核验等方式,对核酸检测...
孙敦秀书法艺术体系研究: 墨派开创与简牍美学的当代重构
发布时间:2025/10/24 头条 浏览:166
引言:两件赠作与一个美学体系的生成
2010年6月,我初次拜访孙敦秀先生于北京寓所,获赠其简牍书法“以史为鉴”。这幅作品以独特的笔法韵律,让我直观感受到简牍书法的美学震撼——它既非碑学的雄浑,亦非帖学的秀雅,而是一种源自笔墨本真的生命张力。十一年后的2021年,孙先生又为我在云南丘北普者黑筹建的“懿陆书院”题写对联,由我拟联,他纵笔成书。两件跨越时空的赠作,恰成为解读孙敦秀书法艺术体系的独特线索:前者凝聚着他对书法本源的思考,后者则展现了简牍美学在当代语境下的生命力。
这一艺术生命的勃发,并非偶然。在《中国简牍墨书史》的后记中,孙敦秀明确提出:“碑派、帖派几千年,今明确提出‘墨派’,三足鼎立。”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书法史结构的重构,更是对书法本体的哲学反思。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孙敦秀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探讨其如何以简牍为基点,构建起一个兼具史学深度与美学高度的“墨派”体系。

一、史学洞见:从碑帖二元到墨派鼎立
(一)对碑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书坛形成帖学与碑学的二元格局。孙敦秀却以惊人的史学洞察力,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古老的书写现场——简牍。他深刻认识到,简牍并非一种僵化的“书体”,而是“篆、隶、楷、行、草诸体嬗变的活态现场与今文字书法的母体”。这一发现,使其艺术探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艺术考古学与书写发生学的双重性质。
在《中国简牍墨书史》后记中,他指出:“前人多写中国书法史,实际上写的是‘碑帖书法史’。”长期以来,书法史的编写形成了以时间、朝代更换为序,以碑帖二元论述为主导的模式。即使到清代康有为等人尝试碑帖融合,乃至当代费新我、孙其峰等人的以帖入碑或以碑入帖,始终“未跳出碑帖的框”,以“旧”的面目维护着两者在书坛的权力地位。
孙敦秀看到碑帖的本质缺陷:“碑帖均是墨书原本原迹刻制描摹、拓印成临摹学习的范本,这种经过若干加工程序而成的碑帖,绝非本来面目,离开了浓淡变化,枯润对比,涨墨晕染,墨气则荡然无存。”这一判断,与宋代米芾“石刻不可学”的醒世恒言一脉相承,揭示了碑帖作为“二次加工”产物与墨书原初生命力的本质差异。
(二)简牍墨迹的史学价值与“墨派”的提出
孙敦秀将中国文字史、书法史的成象途径归纳为“刻、铸、墨书”三大系统,并指出唯有墨书为“翰里之道”。他引用王国维“中国纸上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的名言,强调甲骨文、碑学、竹木简牍墨书的出土对书法史产生的革命性影响。自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发现汉晋简牍,至七十年代后数十万枚简牍的出土,简牍学已成为一门新兴显学。
在此基础上,孙敦秀明确提出“墨派”概念:“简牍墨书完全可以与汉魏碑版和宋元明的各种丛帖鼎足而三”。他指出,简牍墨书中蕴涵着丰富多变的用笔技巧,充溢着书写者心境的流露,其不受后世法度束缚的自由伸展,在有限空间内展现出独特的疏密关系与空间美感。这种“率真的质朴风格”,正是墨派美学的核心特质。
正如当代国学泰斗饶宗颐所预言:“21世纪的书法是简帛学。”孙敦秀的《中国简牍墨书史》正是为此发出的“鼓与呼”,其目的不仅是填补学术空白,更是为书法史开辟第三条道路——墨派大道。
二、美学核心:“因像求意”与“得意忘像”的辩证升华
孙敦秀的创作理念,核心在于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言意之辨”创造性地转化为书法的“象意之辨”。这一转化过程,建立在对简牍墨书特质的深刻理解上:“墨书不受后世森严法度束缚而自由伸展,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出独特的疏密关系与空间美感。”
(一)“因像求意”的实证阶段
在“因像求意”的实证阶段,孙敦秀通过对仰天湖楚简、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的深入学习,破译其背后的“笔法基因”。这个过程犹如科学家的实验室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他曾在谈及创作时说:“每个字都是一个生命体,我们要做的是唤醒它们,而不是简单地复制。”
这种“唤醒”的过程,是对简牍书写者当时的心境、动作、工具乃至文化语境的全方位理解。他常常在工作室中对着同一枚简牍临摹数日,只为体会那一瞬间的用笔力度与节奏变化。这种严谨的态度,源于他对简牍墨书价值的深刻认识:“这些书于竹木简牍(帛)的墨书印记,不仅是墨书史的实物见证,更是溯源中国书法史、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生动诠释。”
(二)“得意忘像”的本体创造
而在“得意忘像”的本体创造阶段,孙敦秀摆脱具体简牍形制的束缚,所“得”之“意”,是简牍书写中鲜活的生命律动、自由的空间意识与质朴的美学精神。既保持了简牍特有的古朴韵味,又在章法布局上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构成感,实现了从“技”到“道”的飞跃。
这种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数十年的潜心钻研,将简牍的内在精神完全内化后的自然流露。正如他所言:“在一个拥有近二千年之久的简牍墨书史和近30万枚出土简牍的国度里,正在为当今书坛注入一新的勃勃生机。”从“因像”到“忘像”,孙敦秀完成了一场从实证到本体的美学升华。
三、形式创造:古典笔法系统的现代转译
(一)“考古学合成”笔法的构建
在技法层面,孙敦秀完成了一套古典笔法语言的现代转译。他的“考古学合成”笔法,将不同时期、地域的简牍笔法融为一炉,构建出丰富而自洽的笔法系统。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杂糅,而是基于对简牍笔墨的深刻理解。在他书写的“以史为鉴”中,可以清晰看到楚简的圆融流动、秦简的藏露参差、汉简的波磔韵律如何和谐共存。
这种笔法的集大成,建立在他对简牍墨书笔法演变的深入研究基础上。他指出:“楚简墨书文字约在春秋中期就已形成了自己的独持风貌…秦简牍墨书演变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两者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他在笔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起笔的多样性:既有楚简的轻盈灵动,又有汉简的厚重朴拙;
行笔的节奏感:通过疾涩相间的运笔方式,再现简牍书写时的自然韵律;
收笔的丰富性:或戛然而止,或悠然远去,每一种收笔都蕴含着不同的情感表达。
正如他在研究中所发现的:“简牍墨书中充溢着书者心境流露的粗细曲直的笔画变幻……洋溢着率真的质朴风格。”这种笔法的集大成,使得他的作品既古意盎然,又充满现代审美趣味。
(二)结体与章法的现代性突围
孙敦秀的“现代性突围”在结体与章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字布排”的原则打破了唐楷以来趋于僵化的结体观念,释放了汉字造型的原始自由。而“小字大写”的技术革命,更是将简牍这一古老书体成功转换为具有展厅张力的艺术形式。
这种转换需要的不只是技法的突破,更是美学观念的革新。在他的大幅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将简牍中特有的疏密关系、错落节奏进行夸张处理,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视觉张力。这种创新正是建立在对简牍墨书本质的深刻理解上:“仅靠墨色的浓淡与简面的留白、交融、碰撞,就构筑起一个纯粹而深邃的艺术世界。”

四、知行合一:理论构建与教育传播的体系化
(一) 理论体系的构建
孙敦秀始终坚持“知行合一”“道术并进”的理念。他的《简牍书法研究丛书》等著作,并非创作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旨在填补中国书法理论史的结构性空白。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五年之久,利用一切可利用之新陈史料,来进行推论的考证,引文的核查,行文的推敲,注释的补正,文字的校对以及新观点的提出。”
这些著作不仅系统地梳理了简牍书法的源流演变,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简牍书法审美体系。他在《中国简牍墨书史》中提出的“墨派”概念,与碑派、帖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理论构建具有开创性意义:“今书法之墨派旗帜已冉冉升起,碑派、帖派和墨派三足鼎立的时期即刻到来。”这种理论勇气源于他对简牍墨迹价值的坚定信念:“《中国简牍墨书史》的撰写正是为此发出的鼓与呼。”
(二)教育传播的体系化推进
在教育传播方面,孙敦秀通过高研班、艺术院和收徒传艺,构建了完整的传承体系。这种体系化的推进,使得简牍书法从个人艺术实践转化为可教、可学、可传播的“学派”。
他的教学不仅传授技法,更注重启发学生理解简牍背后的文化精神。他常说:“简牍不是用来模仿的,而是用来理解的。理解了,你就是简牍;不理解,你永远在简牍之外。”这种教育理念,正是建立在他对简牍书法本质的深刻把握上:“中国书法史诸多悬而未决的课题,让我们通过简牍墨书求解这一艺术的历程。”
五、艺术价值的当代重估与个人体验
(一)以创作代史论的艺术实践
孙敦秀的实践,本质上是“以创作代史论”。他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简牍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核心枢纽地位,重塑了我们对书法流变的认知。其作品中的“拙”与“力”,是对秦汉文化中雄浑、质朴、刚健精神的召唤,为被帖学柔化、因袭之风所困的当代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艺术价值的重估,建立在他对书法史演变的独到见解上:“简牍墨迹中可释读出中国书法发展的脉络、诸多书体的‘家谱’和基因密码。”他通过创作实践,揭示了简牍作为“今文字书法母体”的历史地位,打破了传统书体演变的线性叙事,展现了多种书体在简牍墨迹中“相伴相生”的复杂图景。
(二)个人体验中的艺术演进
从个人体验而言,十一年间两次获赠作品的经历,让我亲眼见证了孙敦秀艺术语言的成熟过程。2010年的“以史为鉴”还带着明显的探索痕迹,那种古朴中略显生涩的笔触,正是艺术家与古老简牍对话的真实记录;而2021年的书院对联,则已臻化境,简牍的基因完全内化为个人的艺术语言,在保持历史深度的同时,展现出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
这种转变,正是艺术家数十年如一日在简牍孤旅中坚持探索的最好证明。正如他在书稿结语中所说:“凡事总得有人去做,总要有人先试先行,这先行一步者不一定是力所能胜者,我深明其理。”
“笔墨当随时代”在他这里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成果。他将北大方正字库作为其新书体的最终归宿,意味着古典美学以最现代的技术媒介,重返日常书写。这种跨越古今的对话能力,在他2010年赠我的“以史为鉴”和2021年的书院对联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这种创新实践,正是对饶宗颐预言的积极响应:“21世纪的书法是简帛学。”

结语:从孤旅到大道——墨派书法的未来展望
从“孤独”走向“博大”,孙敦秀的书法艺术,是一条由“器”入“道”的完整路径。他从简牍这一“器”物出发,经由“因像求意”的实证功夫,最终抵达“得意忘像”的艺术自由,创立了具有当代精神与古典魂魄的“新简牍书体”。
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书法文化的重构者。他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树,成功地使简牍这一古老的书写遗产,从考古学的橱窗中走出,转化为活生生的、能够参与塑造未来中国书法形态的创造性力量。正如他在《中国简牍墨书史》后记中所展望的:“伴随地下竹木简牍的继续挖掘出土,更是简牍墨书研究中的荦荦大者。”
这条探索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他始终保持着学术的清醒:“此书只能是一种尝试,在书法界众多的博学通人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面前可能是班门弄斧。”正是这种谦逊与执着,使得他的工作超越了个人艺术成就,成为一场关乎书法本体的文化重构。
这条从简牍孤旅中开辟出的美学大道,见证了一个艺术家如何通过个人的执着探索,唤醒沉睡两千年的书写记忆,让古老的笔墨在当代重新获得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孙敦秀不仅重构了个人的艺术语言,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书法本质的路径——书法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文化精神的延续与创新。
正如他对助手和出版社的深深谢意所体现的那样,这条道路需要众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碑派、帖派、墨派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孙敦秀已为我们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必将为未来中国书法的发展提供无尽的启示。
作者:黄懿陆